■ 吴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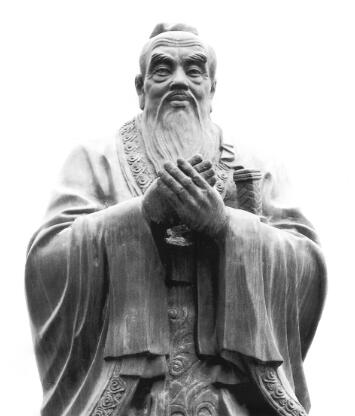
一直都很喜欢《齐物论》这一篇,觉得庄子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规律。所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高下,善恶,美丑、宽窄,这些东西都是人所定义,没有高就没有下,没有善就没有恶,没有美就没有丑。这些东西必须相互依存才可以有其显示其意义。比如,一截一米长的棍子,你说它是长还是短?必须有其他长度的棍子相比较才定义它是长还是短。所以孤立的,没有参照的事物是无法用高下,善恶,美丑来定义和描述的。反过来讲,不管你认为这截棍子是长还是短,对于这个棍子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就是那么长的一截棍子。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相对的东西总是在变化,但之于事物本身却没有意义。解释这个概念,庄子的原文中有“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 可以看到,这些相对的东西是相互依存的。
其次,过分纠结于相对的东西就容易钻牛角尖,因为假如名字可以代表一个事物本身的话,那么这个事物可以有无数个名字,哪一个是这个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如《齐物论》开篇所言的那样,“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一阵风吹过,经过不同的地方,激荡出种种不同声音,哪一个声音可以代表风本身呢?不能,都不能。所以,就如《逍遥游》中所说的,“名者,实之宾也”。不能纠结于事物外在的名相,而要看到它最本质的东西。进而就有那句非常有名的论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即是说,假若以名相来认识世界,那么世界会是复杂而混乱的,因为用这样的方法认识不到本质。
然后,假如执心一念钻于一处,就会发现事物是无限可分的,无有穷尽。就如《齐物论》中所举例子,“百骸,六藏,九窍,赅而存焉,吾谁以为亲?”假如一个人说,他爱他自己,那么他爱的是自己的什么?百骸,四肢,六藏,九窍?哪一个爱,哪一个又不爱?所以,靠无限细化,解剖学的方法也是无法认识到本质的,反而更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相对的东西必然必然是有同一性的,没有同一性就无法对比,那么既然有同一性,那么他们就可以归为同一类。所以,“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所以,“夫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所以,以小大寿夭而论,秋毫与泰山,彭祖与殇子,其实都是一类,至于谁大谁小,谁寿谁夭只不过是评判方法的问题而已。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到,世间所谓的名相基本上都是相对的,善恶是相对的,大小是相对的,美丑是相对的,只是人的定义而已。人的定义一定正确吗?很大程度上,不。法律一定代表公正吗?不一定,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律师拨弄唇舌,摆弄是非。所以,执着于世间所谓的是是非非的东西,是无助于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的。所以,“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