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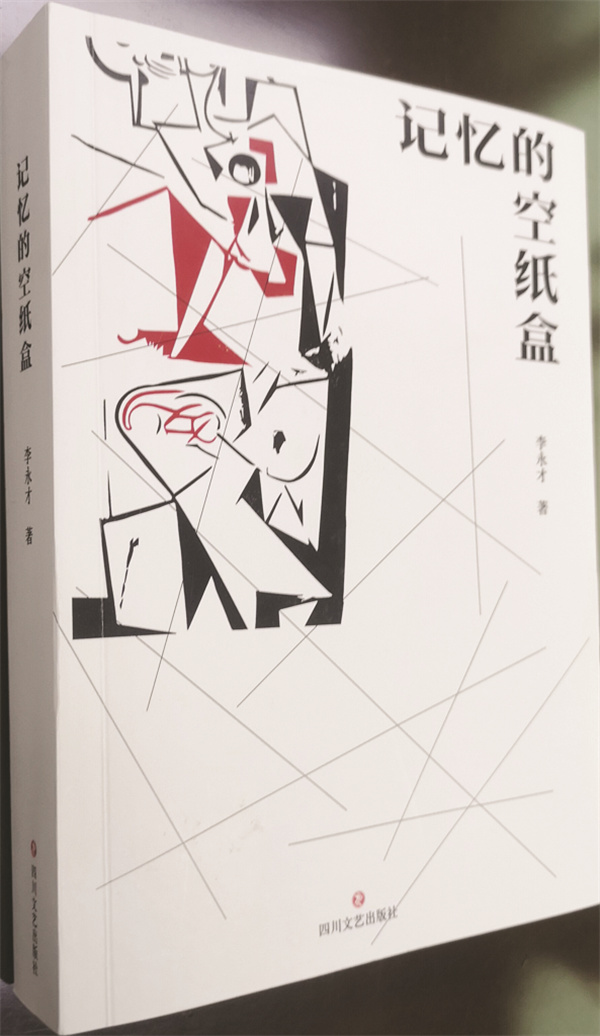
无论怎样的环境生态重组和怎样的内心焦虑色变,诗歌语言在少数那里已经蓬蓬勃勃地开始了新的修辞裂变,诗人李永才《记忆的空纸盒》所暗自渗透出来话语底色,呈现了当代诗人对于时代诸相的细节磨砺和思想打探。受地域气息和种族文化的影响,诗人的生存轨迹伴随着身份的迁移,最后落脚到语调,诗人李永才的血质中,流淌着土地的纯朴和韧性。尽管,在漂泊不定的都市中,他的忧伤和孤独已经变成另一种语言多维变脸。《记忆的空纸盒》所呈现的个人精神成长历史与诗人的书写轨迹是当代诗歌话语艰难的现代化进程的微观透视,从自然主义出发,到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直逼现代主义。诗人李永才在修辞微观之中遭遇了诗歌大道的洗礼,他的诗歌经验综合了童年的土气、江湖的侠气、诗人的豪气、文人的雅气以及作为艺术家的静气和匠气。所以在他近年来的写作之中处处透露出来的语言观念的更新和无论题材还是手法上的有意探索等艺术突围,都表现了个体诗人写作对当代生活的发现惊奇,和诗歌在处理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上的个别命名,同时表达了一代诗人在新语境之中自我变革与文本创造的辩证中的文化抱负和艺术野心。
有哲人认为,记忆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诗人李永才诗歌的记忆,是诗人全景式的写作尝试。诗人拉网式的精神诉求,在疲惫的日常之中展开,从城市到乡村,仿佛一种精神的溯源。作为汉语的乡愁,是关于乡村与城市的魔幻,正如美国诗歌从迷惘的一代,到垮掉的一代,到新时代汉语诗歌如诗人霍俊明所命名的“尴尬的一代”。在强大的农耕文化背景之下,历经苦难的汉语正处于一种“迷惘”与“尴尬”的“双重焦虑”中,今天的书写已经不是简单的异化和去魅。诗人李永才的书写逻辑,跳出了传统乡村诗歌简单的赞美和修饰的忧伤范式,既有缠绵,又有反思批判。关于城市,我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幽默的外乡人”的内敛和机智。所以他的诗歌有一种距离上的漂泊感,也带来李氏某种“飘忽的诗风”。正如《西西里的故事》所表现的故乡,不是因为它是诗人的出生地和祖先的尸骨埋葬地,而是我们爱的出发地,是我们初爱的地方。诗歌的记忆,恰恰是诗人现实的五彩斑斓,是孤独灵魂的辽阔牧场,记忆是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是如杜甫一般入世情怀。尽管诗人李永才的诗歌中情感的成分非常浓厚,但是“一介贫穷书生光脚在乡村走了二十年,又在城市挣扎了二十多年,还是老老实实看几本书,写几首诗”的深刻内省,仿佛有些历尽沧桑的感觉。“我无法在精神的盒子里/挽留一粒命运的阳光/只想装一分淡泊,三分宁静/让一个人的记忆,白云一样散落”。空,是放下,是悟道的空灵。“空盒子”仿佛语言的诗歌,是诗人理想与梦幻落脚点,诗人最终皈依了“人生之空”,似乎也应兑了中国文人如大潮一般悠久的天人合一的思想。身处后疫情时代,风云变幻,心性磨损,儒释道的生命调式,似乎成为当代中国诗人某种难以逃避的悲壮而残酷的语言宿命。
李永才属于情感型诗人。华兹华斯认为,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重庆人火热的性子、四川人的麻辣味和狭义心肠,包括如袍哥一般地缘文化的熏陶,所以李永才诗歌的抒情性是从他娘胎中带来的。他的诗歌节奏缓慢,语调铿锵。偏向情感一隅的窃窃私语,总是寄托于具体的事象、人象与物象上。“我苦涩生活的一部分/需要说出来的/——已经成为飘逝的尘土”,他的乡村意象的经营饱含了对于亲情、土地和河流的感恩之心。“在蔚蓝的苍穹之下,播种光与影/在红湿的雨声中,体味虚与实/将过去的荒诞、不堪和愧疚/重新回忆一遍”,他的城市意象变幻莫测,带着个人的感受和体温。“而我只想读流云与天色/如读一匹老马/穿梭于驷马桥与九眼桥之间/那一排卷进风尘的树/在神思倥偬里,早已失去真身”。在现实中读出了烂漫的忧伤。实际上是“贫穷和苦难,养育了一个少年/浪迹天涯的忧伤”。尽管四川诗人身上有一种“山头意识”,有一种“扛旗子”的传统,但是无疑为他们的创造性提供了善良的温床。诗歌的民间精神在四川大地风起云涌,生生不死。诗人李永才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东方诗社开始,已经步入了诗歌先锋建设的行列。应该说,《记忆的空纸盒》是诗人李永才文学认知和诗歌修养的全部表达,是诗人里程碑式的作品。
李永才的诗歌之中有一股强烈的60后味。无知的童年(但有更多的时间投身于大自然的细微之中),饥饿(精神和肉体)的少年,劳累的中年。中国经济的转型和高考制度改变一代人的命运。贫穷总是伴随着孤独,同时磨砺了生存意志,从四川师范大学到北大求学。他的心路历程充满了对理想生活的渴望,所以他的诗歌之中总是隐隐约约地散发出淡淡的忧伤,和大多数60后诗人一样,他的诗歌永远充满了挣扎,以及对命运的反抗。“我看到了,藻类云集水草翻涌/如此汤汤的世界/失败是有限的,/而生机是无限的/潮涨潮落,仿佛人世代谢/推近及远,往复循环”,抗争之中带着几分坦然和自我劝慰。“诗歌的活力发生在词与词的组织间,但照亮这一切的是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力、价值创造力。”(姜涛语)。多年的语言生活锻炼以后,他的诗歌从情感空间转型为文化空间的精神密码的重构。所以,诗人才会在人间稀疏的烟火的悲悯之中,看见了时光的伦理。“生活正在变得,如此的荒谬/如果你想看天空/云朵就是脱脂的牛奶,在桌面上流淌”。从诗人李永才的诗歌转型的写作个案,我们可以窥见作为60后诗人的话语形态在澎湃的时代特征之中如何完成语言对自我的塑造。诗歌如何关注知识和后工业时代的命运,是60后诗人写作必须面临的诗学难题。诗歌的困惑,不仅仅停留美学和技术方面。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代诗人在写作进入中年以后,开始迷恋“反转的诗学”。他们貌似二三流的作品,其实是在抵抗时间对生命的侵蚀。李永才的内心其实装有多少如一江春水般的万般无奈与柔软。身处在无边黑夜的我们彼此是看不见的。除非有一次被如闪电般的语言照亮。青春期的激情万丈,冲动的语言,转变为轻盈的晦涩,甚至走出了公共话语视野,变得十分难懂。
“生命不止是一只散佚的候鸟/许多雨季过去了。我喜欢的旧报纸/旧马车,云蒸霞蔚的旧日子/都成了十字街头的遗梦。”,生命的沉重影响了语言的沉重。语言与生命合一,诗歌从文化转型为语言之诗歌,诗歌回到了诗歌的怀抱,道成语言,语言成为诗人的精神家园。“下午是蓝色的,风声也是/我执念于一溪云,半江春水/无声无息。闲情甚多,仍需一分淡定。”,诗歌是诗人一次又一次的心灵栖居。“60后,这个代际的诗人写作优势在于,他们有足够的人生经验,数十年的写作训练能够轻车熟路地将其转换为诗意,这个群体早已经过了为名利写作,趁着灵感与才情写作的年龄,过滤掉生命中的喧嚣和尘埃,诗成为建设人生的一种方式”(王单单语)。你在李永才后期的诗歌之中,看得到明显的美学趣味和修辞功力,尽管距离语言的伟大,我们都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