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名片
陈曼冬,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杭州市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出版书籍:《见证:使命与方向》《中国城市文化消费报告:上海卷》《遍看繁花》《杭州工人运动历史》《惠民济世》等。
■ 华东周刊 李 洁/文 朱旭洁/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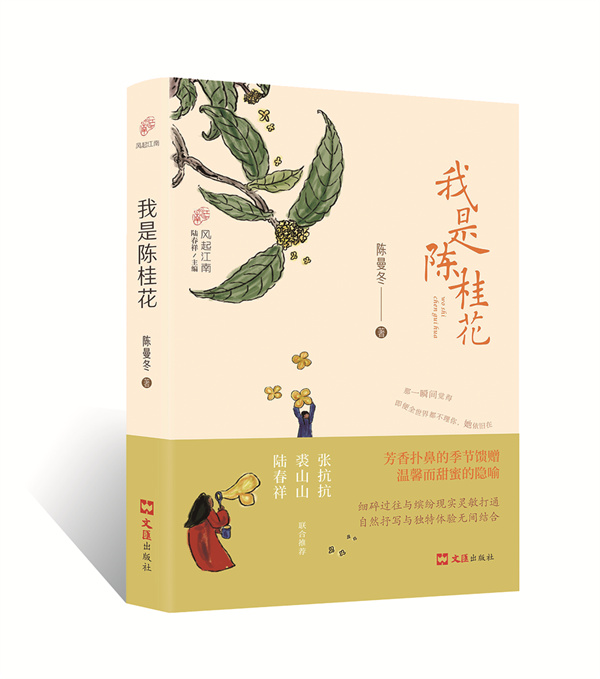
陈曼冬著:《我是陈桂花》
“在杭州这座城市,桂花开了这件事情是可以上新闻的‘大事’。大约是桂花开了才代表秋天真的来了吧。”陈曼冬在散文《桂花》中这样写道。在她看来,仲秋时节,桂花悄然开放,这座城就像浸泡在蜜罐子里一样,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
对于桂花,陈曼冬有特别的偏爱。桂花是杭州的市花,也是作家陈曼冬的笔名,甚至朋友们都喊她陈桂花。今年,桂花飘香的时候,陈曼冬的新书《我是陈桂花》出版了。
《我是陈桂花》是一本散文集,收录了陈曼冬近两三年写的文字。她称这本书为“缝隙里开出的花”——这些文字大多数都是在时间的碎片和生活的缝隙里完成的。在书里,她写到了咸鸭蛋、杨梅、折耳根、粽子、桂花……记录了思念、往事,青春、人生。
陈曼冬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小生活在杭州,从小热爱写作。她曾在北京生活过十几年,在那里读完了大学,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后来为了父母,她回到了家乡杭州,从此定居下来。很多的童年记忆,家族往事,也记录在了《我是陈桂花》中。
她说,在生活的缝隙里,在工作的缝隙里,在时间的缝隙里,热爱文学的种子不断地生长,然后开出了花。想来,《我是陈桂花》就是其中绚丽的一朵。
正如浙江省作家协会诗歌专委会主任、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昌建所言,“读着《我是陈桂花》,喝着桂花酒,然后读几篇书中的文字,这个秋天和这本散文,那真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写作与桂花如何塑造着我们的生活?以下是杭商传媒对陈曼冬的专访。同时,一起来品读陈曼冬的作品《桂花》。
华东周刊:你的很多身份都与写作有关。你是何时爱上写作,如何爱上写作的?
陈曼冬:小学一年级,我在《小朋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得了第一个写作的全国性奖项。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偶然还是必然,总之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开始被老师和家长朝着“这个孩子写作文挺好的”方向去培养。以至于学生时代同学的父母见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班级里作文写得最好的孩子。”而我也顺水推舟,以为自己真的长大了可以当作家。那些年里经常会有一些类似于《我的理想》这样的命题作文,作文里我的理想一定是成为一名作家。因为如果不这样写,似乎就不对。
第一次让我真正思考我是否真的热爱写作这件事是小学五年级。虽然那时候写的仅仅是作文。少年的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写作文上——第一次独立过马路、第一次撒谎、打扫班级卫生被安排在不喜欢的岗位……一切皆可写。
我不停地写,日记本摞成了高高的一叠。而与此同时我的数学成绩直线下降,大约是我把用来做习题的时间也给了作文。于是我的父亲发火了,他说不要写作文了,把数学成绩补上去再说。
究竟那次之后有没有停止写,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数学成绩都不太好。而也是那次,我第一次发现我不能不写——因为日子那样丰满而有趣,我必须把他们记录下来。
中学时代语文课的作业里有一项是周记,一周写一篇作文。通常来说周一交上去,大约到周三、周四本子发还,接着写新一周的周记。可是我每次都等不及,去问老师,本子怎么还不发下来呀,我想写作文了。再后来我是那个唯一有两本作文本的人。
第二次让我思考写作这件事,是中学时代的一次考试。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路》。大约是对于自己过于自信,我几乎没有审题和打腹稿,洋洋洒洒在作文里写了一条虚幻的未来之路。几天后卷子发下来我傻眼了,满分40分的作文我只得了16分。少年气盛,我拎着卷子推开了语文教研组长办公室的门,我问,为什么。
也就是这一次,老师第一次同我探讨起文学创作与应试作文的异同。这一次的交流对于一名少年是多么的重要,大约是人生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开始思考关于“写作”这件事。如果说之前只是凭着热爱和强烈的表达愿望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么这一次让我开始意识到“生活表达”与“写作表达”的异同。
很多年之后,今年夏天我与当年的那位老师聊起了这桩往事,老师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件事,但他依旧是欣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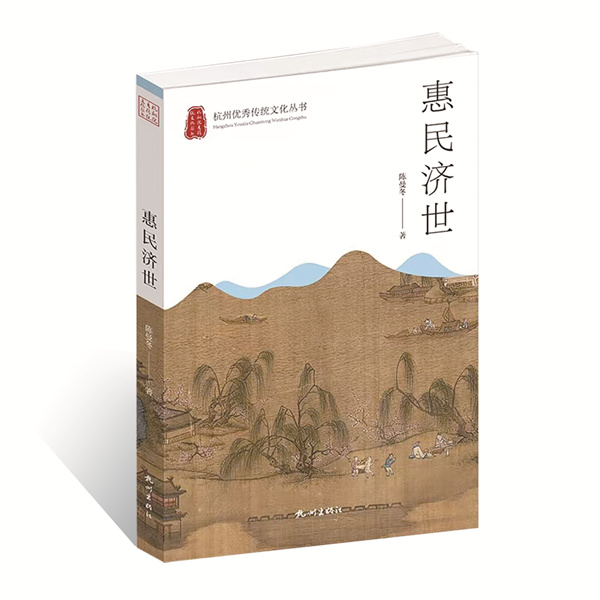
陈曼冬著:《惠民济世》
华东周刊:写作这么多年,你始终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见证:使命与方向》《中国城市文化消费报告:上海卷》《遍看繁花》《杭州工人运动历史》《惠民济世》等书籍。写作对你来说为何如此重要?
陈曼冬:现在,我的职业是一名文学工作组织者和服务者,对于我来讲,写作是必须的。因为我无比地热爱作家这个群体。他们永远天真,永远善良,永远热泪盈眶。他们用思考和文字与这个世界交换着彼此的看法。他们之间是有一种特殊的沟通介质的,这种介质就是写作。我以为唯有写,才是到达写的唯一途径。唯有写,才是与写作者沟通的语言。
我始终觉得热爱文学的人是幸运的。写,是因为有话要说,文字就是一道出口和一种释放。同时文学对于我,又是可控的,有安全感的。文学本身指向着真理,有纯粹的美感,文学里的道德是可感知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时候文学比生活更美好。
华东周刊:桂花既是芳香扑鼻的季节馈赠,也是一种温馨而甜蜜的隐喻。朋友们都称呼你“桂花”,陈桂花也是你的笔名,甚至你的微信名也是桂花。“桂花”这个名字是怎样来的?
陈曼冬:被唤做桂花,其实是源于旧同事。当时我在北京工作,是一名大学教师。某一年的秋天和北京的同事一起出差杭州。在微雨的黄昏,路上突然间闻见桂花香的。那香味儿,起初若有似无,羞羞怯怯的。忽然一阵风来,吸进鼻子的,是大把大把的香甜。我于是说,呀,桂花开了。那熟悉的香甜味,率真,浓烈,让人欢喜。
我抬头找,眼前恍恍惚惚的,有一树花开,细细碎碎的,是一树丹桂,花香雾般飘缈。仿佛只需一棵树,就染香了一整个江南。北方来的同事没有闻过这样的香味儿,兴奋极了。她说第一次知道桂花,是毛主席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她学到这首词的时候,老师只是讲桂花酒是一种用桂花酿造的美酒,但桂花树什么样子的,估计连北方的老师也没有见过。
忽然她扭头看我,看得我发毛。我问怎么了。她兴奋地指着我说,“就是你呀,香香、甜甜、糯糯;时而飘渺,时而浓烈。就是你啊,桂花!”
后来回到杭州。注册微信名的时候用了桂花二字。杭州到底是桂花的故乡,周围的小伙伴儿老伙伴儿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唤我做“桂花”,这在北方是从来没有过的。他们叫我桂花,我便应着。这一应,便应了6个年头。在杭州几乎所有人都爱叫我桂花,我想是这城里的人,真的是爱着这小小的花儿吧。
华东周刊:最近你的新书《我是陈桂花》出版了。书中,你将细碎过往与缤纷现实灵敏打通,将自然抒写与独特体验无间结合,字里行间不时跃动着智慧、热情、温暖、善良、情趣。你为什么说这本书是“缝隙里开出的花”?
陈曼冬:《我是陈桂花》是一本散文集,收录了近两三年里写的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大多数都是在时间的碎片和生活的缝隙里完成的,事实上书里很多内容,描绘的也是这样的缝隙。
我所说的缝隙,更多的是一种时空空间。比方说在家、在上下班的路上、在旅途中、甚至在排队等待时……在任何内心和思维存在的地方。我理解的这个缝隙是对于理想生活的追逐,亦是享受当下的世界。比如泡一瓶梅子酒享受时间的馈赠;比如看老照片想象那遥远的过去;比如读诗;比如看电影;比如看小猫咪体会它追逐自己的尾巴的欢乐……我用这样的缝隙,抵御繁忙、琐碎甚至有些糟糕的日常。
在这个越来越卷的时代,我经常会思考,工作的终极目的究竟是什么。虽然很多不了解作协工作的人以为我的日常就是看书与写作——且不论如果日常就是看书写作,那么也许看书写作就没有这样美好了。我始终认为如果能从工作中获得力量和快乐,并从中得到满足感,应该是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以为我是幸运的,虽然我们都一样的忙碌、琐碎以及有各种各样的求而不得。
可以这样理解“缝隙里开出的花”:在生活的缝隙里,在工作的缝隙里,在时间的缝隙里,心里的那颗从少年时代就萌发的热爱文学的种子不断地生长,然后开出了花。
桂 花
陈曼冬
“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
在杭州这座城市,桂花开了这件事情是可以上新闻的“大事”。大约是桂花开了才代表秋天真的来了吧。仲秋时节,桂花悄然开放,这座城里就像浸泡在蜜罐子里一样,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花香。
一
桂花不以艳丽的色彩取胜,更不以婀娜的身姿迷人。那么精小,那么极致,星星似地点缀于绿叶之间,显得那么自然,安排得那么恰当,简直就是上帝的艺术品。只要路过有桂花树的地方,远远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桂花香味。一般说来桂花分为四种:金桂、银桂、丹桂和四季桂。金桂的花是柠檬黄淡至金黄色的,花色偏黄,香味浓郁;银桂花色偏白色或者淡黄色,花后不结实;丹桂的颜色最深,花色较深,有橙黄、橙红至朱红色,气味却是最淡的;至于四季桂,顾名思义,四季开花,香味倒是不及金桂、银桂以及丹桂这般浓郁。
桂花树上茂盛的,桂花却是小小的。路过桂花树下只闻阵阵花香,但见片片绿叶,却不见花开何处。于是不由得靠近细看,一丛丛小巧玲珑花蓄如少女低眉浅笑,相互呢喃。
桂花虽香,可花期却不长;想要留住这股香气,传统的办法是将其酿成糖桂花。
小区里就有许多的桂花树,高的部分够不着,便采一些近处的桂花。事实上也不用采摘,盛开的桂花多不结实,轻轻一抖枝干,桂花便扑扑簌簌的往下掉。遇有微风吹过,便落在发辫上、脖颈窝里,抹也抹不掉,捋也捋不尽,那股微醺微甜的香气许多天都盈盈于袖,不绝如缕。
如果说采集桂花尚算得上是桩风雅之事,那么之后的清理过程就不怎么有趣了。刚摘下来的桂花里有许多杂质,甚至还会发现几只小虫子,这些都需一遍又一遍地捡干净。随后,将选好的桂花平铺在筛子里,置于阴凉处晾干。至花色变深时,用手搓一下,有柔润感而无硬物感时便可。
接下来,就是腌制工作了。按4斤桂花配1斤盐的比例,放入梅卤(腌过青梅的卤水)中。酸中带咸的梅卤,能很好地中和掉桂花略有的苦味。半个月之后,取出桂花用水漂洗一下,再将其晾干。经过这番处理的桂花,除了能保持原有的花香,花色也依然鲜艳,且不会发黑。然后找一个干净的广口玻璃瓶,一层桂花一层糖(白糖的用量要多于桂花),依次码好,并用汤勺或者擀面杖压实。从紧实地旋上瓶盖那一刻起,糖桂花便替代了对甜蜜一词的所有遐想,一有空便会去看看它。瓶里的白糖和桂花晶莹剔透地交织在一起,一层金黄一层洁白,精致灿烂。在经历了与白糖数个日日夜夜的对话后,原本饱满的小花瓣渐被磨去了脾性,沁入了融化的糖水,与之混合落入瓶底。再等上十多天,瓶底那些美美地吸收了糖水的桂汁已变得蜜一般黏稠细密,透着宛如琥珀的金黄色泽,引人垂涎,糖桂花终于做好了。
小心翼翼地拧开瓶盖,刹那间,空气中便弥漫开阵阵淡雅的香味,甜丝丝地沁人肺腑。我是很喜欢这股清甜滋味的,这馥郁的桂花香正是秋天味道的延续。小时候晚上看书迟了母亲会做一碗年糕汤或者番薯汤,热气腾腾甜甜蜜蜜地喝下去。这些甜汤的点睛之笔,便是糖桂花了。有了糖桂花的帮衬,嗅觉和味觉都会立刻丰富浓郁起来,也平添了几多气质。
闭眼试想,一个小小的青花瓷碗里,汤汤水水的面上,零星散落着五六瓣细小的糖桂花,经热气一逼,立即弥漫起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未吃先已醉人。待得一勺入口,那独特的桂花香便在口舌间绵延缠绕,由内而外地熏袭着人的所有感官神经。朵朵桂花在汤水中上下浮动,看得我竟然也是有些动容的。
二
《迟桂花》是郁达夫在年近不惑时创作的小说,被誉为郁达夫在艺术上最精致成熟的小说。彼时的郁达夫,人近中年,韶华已逝,创作风格的改变,究其原因离不开岁月的沉淀,过往的人生给予了他内心的豁达。
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实际上在我们的人生中,很多东西都来得迟,领悟得迟,但那些迟来的获得未必就是哀伤的,正如迟桂花,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
小说的开篇是翁则生写给老郁的信。历经了几番大起大落的翁则生,对于现实,不求反抗,只求安宁。僻静的翁家山养好了翁则生的身体,也修养了他的心性。正如那青葱的山和如云的树带给人的清新淡雅,翁则生面对人生是沉静坦然的,他享受着淡淡的平和与甘甜。他是一个积极的遁世者,在逃避现实中找到了自我,在世俗中安放了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中年的翁则生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虽然健康、事业、婚姻都来得很迟,但这些前半生错失的精彩一齐充盈着他人生的下半场。犹如迟桂花的清香更为醇厚,人生在苦难之后是云淡风轻。
老郁在前往翁则生家的路上,闻到了迟桂花“说不出的撩人的香气”。翁则生的妹妹翁莲成长为一株现实生活中的“迟桂花”,无论身经怎样的纷争与磨难,她的内心始终保持着迟桂花一样的芳香纯净。她像迟桂花一样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就算在冷僻的山里也能芳香四溢,无论生活如何变幻莫测,她总能释放自我,保持天性,在有限的空间内找到无限的自由与幸福。
老郁生活于“煤烟灰土很深的上海”,去往僻静的翁家山参加朋友的婚礼,对老郁来说是一场有意识的心灵之旅。在我们以为老郁会与翁莲发生身体上的关系时,郁达夫对欲望的描写却戛然而止,继而转折为灵魂的净化。与其说是纯真质朴的翁莲唤醒了老郁的“邪念”,倒不如说是老郁在吐露发泄了压抑的欲望后,内心获得了一种久违的释放。
“但愿得我们都是迟桂花!”这句话像是郁达夫深情的呼唤,呼唤那些逝去的青春,也呼唤可期的未来。翁则生、翁莲、老郁都在生活的坎坷和世俗的纷争里获得了重生,或获得健康与爱情,或收获亲情,他们都在对自我的剖析与完善中找到了未来人生的激情与信心。人生中有些光亮总会被障碍物遮挡,但请一定向着光亮走。
三
“桂花树,我要向你表白:你崇高而珍贵,普通又特殊,但又混杂于众树之间:这恰恰是你的可贵!”这份表白来自于阿多尼斯。是的,就是那一位说出“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的伟大诗人。这位白发苍苍的叙利亚诗人将他首部中国题材长诗取名为《桂花》。
2019年11月1日晚间,89岁的阿多尼斯在带着这本书出现在杭州单向空间。诗人有的时候就像是一位哲人,只言片语地为迷茫的人们跳脱现实的困顿指出一条路径。如此一来,读者收获的便不仅仅是一缕泛着桂花味的书香。
阿多尼斯在字里行间诚意而又热切地借此表白:“你崇高而珍贵,普通又特殊,但又混杂于众树之间:这恰恰是你的可贵!”桂花,是属于中国的意象。可为什么一定是桂花呢?是因为诗人总是拥有比常人更敏锐的嗅觉吗?《桂花》的诞生也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其创作灵感直接源自阿多尼斯去年九、十月间的中国之行,尤其是皖南和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以及所到之处的遍地桂花香。全诗字里行间随处流露出他对中国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的热爱,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情谊。
不过,这些都是明面上的原因。甚至,不能称之为原因。只是恰好的时刻发生了恰好的事情。深掘诗的世界,总能不断发现比字面更大的世界。“在阿拉伯文化中,因为一颗苹果,树和女性都成了罪恶之源。我之所以用桂花这株植物作为书名,是要赋予她完全相反的意义。就像大诗人伊本·阿拉比赞美女性的诗句:‘一切没有阴柔气息的地方都是没有价值的。’我用桂花来命名长诗,赋予世界女性气息。”
诗人的世界果然离不开女性。
在单项空间阿多尼斯的第一声问候就是献给到场的“女朋友”们,并强调:“我最爱的是无名的女性,我所爱喝的酒,我所爱的女性,她们的精神存在于万物之中。”而他的笔名“阿多尼斯中文意为“年轻的美男子”。如此一来,即便他今年89岁,10年后99岁,几十年后再也不在,大家聊起他的时候,依旧会喊他作“年轻的美男子”。
在现场浙江大学教授诗人江弱水欣赏他的笔触和思维。他试着剖析阿多尼斯的诗篇:“有非常精粹的压缩性书写、跳跃性很大,格言式的写作归纳性特别强。像在用东方绝句的联缀书写方式,在现实、历史与传统的深刻反思里来回跳跃。”听了夸赞阿多尼斯却诚实地表示:“我对自己的诗歌没有做过系统的思考,但是觉得你说的非常好。”幽默的话语,惹得现场一阵哄笑。
“献给薛庆国”——《桂花》的扉页上,印着这一句献词。多年前我有一个诗歌推荐的专栏曾经推荐过阿多尼斯的一首诗《致西西弗》,翻译就是薛庆国。讲到西西弗逃不开的便说关于精神层面的东西。诗歌精神,不是肢解诗歌器官;也不是热衷以小圈子划分诗的地盘;更不是要在一首诗里翻读出一段时间、一种观念、一个流派。如果这个世间能够存在少数有着诗歌精神的诗人,那么他们一定是尽力在保留纯洁的人。就像阿多尼斯说的那样,经受高热和火花的炙烤,在失明的眼眶里,寻找最后的羽毛。对着青草、对着秋天,书写灰尘的诗稿。
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有点像迟桂花:因为开得迟,所以日子也经得久。(部分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