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阳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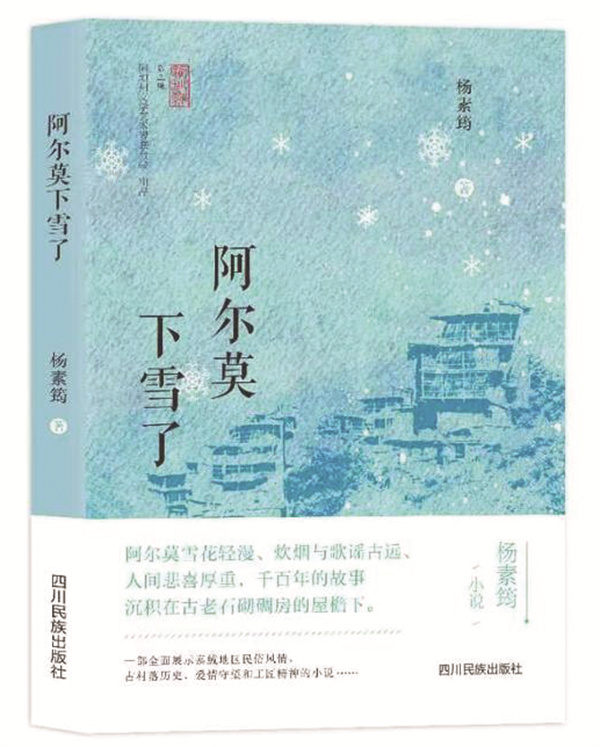
阿坝女作家杨素筠在书的后记中袒露心扉:“对一个美丽而历史悠久村庄的钟情,是自小就刻进我骨子里的情感,所以我写下这部小说《阿尔莫下雪了》。”故事,就在纷纷扬扬的纯白雪花中,在美丽而古老的藏地村落里,徐徐展开。
杨素筠的文字清丽,富有散文语言的美感,她似乎有意贯通小说与散文的壁垒,让故事情节像春天的树叶自然而然地生长,不经刀斧,不着痕迹。《阿尔莫下雪了》看上去有梦一般的质地:大雪落下,两个老兄弟阿让斯巴丹和琼若木尔斯甲在阿尔莫村落最古老的石碉房里围火闲聊,一帧帧往事从记忆中浮出水面,铺展开来,竟是漫漫一生的藏地守望。
以人心的承诺抗衡无垠岁月
小说主人公阿让斯巴丹一出场,就借师兄琼若木尔斯甲的话来赞扬他:“这些年,你将熊茹家的笔画绘制成这么多的卷轴画,一幅一幅保持得这么完好,你是花了大半生的心血来照顾它们啊”。六十多岁的阿让斯巴丹的确已花了四十多年时间来临摹壁画,将卷轴画存放到阿尔莫石碉房的经堂中。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读者了解到阿让斯巴丹的执着,来自于他对艺术的真正挚爱,对师父的郑重承诺,还有对妻子罗罗斯基的生死眷恋。罗罗斯基同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天赋,但身为藏地女子,她很小的时候就清醒地明白,自己要种地、做家务、带孩子,从早到晚都有忙不完的事,无法像男子一般坐下来,气定神闲地画唐卡、临壁画。阿让斯巴丹与琼若木尔斯甲一道,曾从少年时代起,跟随师父熊菇柯普仁青学习木匠、绘画和木雕等手艺,整整八年时光,与师妹罗罗斯基朝夕相处,他俩不约而同都爱上了罗罗斯基。就连师父师母面对两个优秀的年轻人都不知如何抉择,最终是罗罗斯基选择了阿让斯巴丹,因为她与他在艺术上更有共鸣,心灵相通,精神世界也能彼此呼应。
小说有个意味深长的情节,当年师兄弟同时出师后,又在同一天与家中长辈一道来师父家求亲。落败了的琼若木尔斯甲黯然离去,但他在师弟和罗罗斯基的婚礼上,重新露出笑容,送上祝福,并表示“我永远是你们的哥哥。”可社队里选折琼若木尔斯甲当了队长,由队长来负责管理大家的集体劳动,琼若木尔斯甲分配给阿让斯丹巴的都是背石头、修梯田、砍烧炭菜等重体力活,他明知身为一个画师,必须细心保护双手,不能过度操劳,他却并未偏袒和照顾师弟,让阿让斯巴丹“每次回家累得站不起,还要绘制壁画唐卡,积劳成疾”。
在整部小说中,琼若木尔斯甲除了这里的“突兀表现”,其他地方都显得大度而宽容,这里看似“不和谐音符”,仔细推敲却格外生动和自然。生而为人,并非斩断七情六欲的神祇,他有私心和愤懑,才显得立体和真实。
回溯昔日心动,少女罗罗斯基也许对两位师兄都有好感,毕竟他们都那么真心实意地对待她、爱护她,并且是父亲的左膀右臂。罗罗斯基选择阿让斯丹巴,与她心中从小跳跃的艺术火苗切切相关,当她在一场春雪中遇难,阿让斯巴丹在崖下洞口找到她时,她拼尽最后的力气对爱人说:“我们的孩子,不要放弃绘画,你喜欢的画,我再不能……”弥留之际的生死重托,使阿让斯巴丹更加坚定了自己肩上的艺术责任,他愿在古老的村落,耗费毕生的时间来履行承诺。
情感交织奔流生命赞歌
阿尔莫的土地,生长青稞和小麦,同样生长灵性。在这里万物有灵,一座古碉楼的组成部分竟对应着人体各结构:第一层属于最底层,这层的石头墙坚固有力,代表人的腿部,坚固有力才能承受上部的重量。底层用于关养牲畜,所有粪便都在一层堆积处理,它对应人的肠肚和排泄部位。第二层是堆放农具和牲口饲料的地方,也有火塘加工草料,保持良好的通风和适度保温,四周也有坚固的墙体,二层对应人的腹腔。第三层是一个家庭议事的地方,有一个大火塘、烤酒坊、陈设各类厨具酒具,在这里烹制美食,制作烤酒,人们围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聚会、开心时也尽情唱歌跳舞,这层对应人的胃部和心脏,主宰健康和情绪。第四至五层建有左右对称坚固的木架粮仓,设有小产房,这两层用于储粮,对应一个人的胸腹,更像是一个母亲的双乳和生育部位。六楼设置一个经堂,经堂旁设置僧房或者小木屋,七楼主要用于煨桑、祈福,存放柏香枝、堆放擦擦、挂置经幡、设小嘛呢堆和风轮转经筒。六层七层好似人的思想和大脑部位。
一座建筑与人之间抹去了界限,就像小说中穿插的阿尔莫传奇故事。关于龙女和白杨树的友谊,白杨树千秋万岁不竭的等待,到了最后,古老传说在阿尔莫重新落地生长,“罗罗斯基仿佛就是那个飞走的龙女,她带走了两个少年的心”。作者由衷地叹道:“也许一些人和故事在阿尔莫存在本来就是一个真实而又神奇的梦境”。人在梦中,也在神话中穿梭,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无隙,于是生长出了如同大海般奔流不息的情怀。
嘉绒人认为布谷鸟是从印度飞来的,它们具有顽固的记忆,“今年飞在哪座山,明年会继续飞到哪座山”。这种神秘的鸟儿,“每年藏历三月八日,它从印度起飞到嘉绒地区来,如果没有来,表示它已经死去了”。布谷鸟身上携带着“至死方休”的浓烈记忆,小红嘴鸦也是这样,“小红嘴鸦一旦在谁家碉房上筑巢,便永生永世不会离开这一家人,哪怕这家主人后来搬了新家,它们依然会随同搬迁。”这些坚贞而单纯的鸟儿,是那么依恋村庄与白杨,阿让斯巴丹相信,风声、鸟声、河水流淌声,“只要村子还有人住着,这些来自悠久岁月里的声音就会永远存在”。
阿尔莫的人与鸟兽牲畜之间,存在一种来自灵魂的平等关系,在古碉房石头墙壁上,会悬挂牛头骨,这是“生前对阿尔莫家立下功劳的牛”。这些奶牛供养大了家里的孩子们,等到它们年老体衰,主人会将牛送到寺庙后面的草场去放生,虽然放生地距离村庄有二十多公里远,但每年冬天来临,老牛依然会回到村子,直到寿尽死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牛不仅仅是“家庭的财富”,它得到了如同家族成员般的尊贵对待,而放生牛的“冬日归家”,是超出了常识的浪漫与深情,与人的情感相融相汇,交织成一曲诗性大歌。
从清风和泥土中生长的爱情
《阿尔莫下雪了》读来清新优美,除了罗罗斯基与阿让斯丹巴的爱情,还有其他许多散落风中的萌动,都令人动容。比如罗罗斯基阿奶的爱情,孙女不解地问阿爷有多爱阿奶时,老人这样回答:“他对我很好,就像吹到我心里的那股清风一样。”阿奶能从风中听到玉米青稞该扬花授粉了,该给屋顶压土添瓦了,该去收割自己家里的玉米土豆了……如果风久等不来,“她会轻轻地为风做祈祷,希望风能平安到达她的村子”。风是阿奶生活中的陪伴,当爱人离去之后,四季的风依然伴着阿奶,她的思念绵长而时时如新,从来不会因为阿爷的离去而褪色。
琼若木尔斯甲家中的女人,仿佛都中了一个命运的魔咒,先是琼若木尔斯甲的父亲,在儿子十二岁时跟人去甘肃做皮货生意,从此一去不回,琼若木尔斯甲的母亲那时还不到三十岁,便坚守爱情誓言,一等就是五十多年,仍然不见丈夫回来。琼若木尔斯甲的妹妹三郎初,与爱画画的伐木工人李明轩真心相爱,李明轩却在一场山洪中失踪,那时两人还未结婚,三郎初怀上了李明轩的孩子,她在心中存有一丝希望,期待爱人会活着回来,便生下女儿拉姆,一等也是几十年。即便这样,三郎初仍未后悔自己的爱情选择,她说:“有些人,哪怕只见了一眼,在脑子里就已经和他过了一生。”
魔咒尚未解除,到了拉姆这一代,她和一个男人通过网络走入现实,为男人生下一个女儿,警察上门缉拿,她才知道自己爱上的是一个犯下了累累罪行的毒贩。男人被判无期徒刑,高墙之外,拉姆却依旧带着年幼的女儿在等待。也许和她的外婆与母亲相似,等待的尽头是一场空茫,拉姆仍然无法说服自己,爱情是这些善良女人们心中的信仰,她们愿以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为祭,将信仰变成一场浩渺的守望。
阿尔莫村落女人的爱情,散发着古老情感的釉光,她们认准了一个人,便将一生一世托付出去,即便托付的是不绝的孤独寂寞也在所不惜,这种执拗与天真,像是从这片质朴泥土地里生长的野花,无需解释,从不迎合,但暗自芬芳。
杨素筠的笔调始终淡淡的,无论描写撕心裂肺的葬礼,还是情感的两相抉择,世俗意义上的大开大阖,到了阿尔莫村,都变成像清风明月一般自然。这个古老残旧的村落,承载了世世代代的期盼,如今随着年轻人背井离乡去城里生活,它似乎一天比一天衰老破败,好在我们看到了光明的希望。大年三十,阿让斯丹巴深深思念的儿子索尔丹不但回来了,还带回一位对古村落历史和古建筑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鲁丽,鲁丽激动地建议:“我们可以努力争取,看能不能在阿尔莫村建一个古村落的民间博物馆,同时展出壁画和唐卡。”
将来的阿尔莫村会怎样发展,还是未知数,可我们都看到了,“新年,阿尔莫村子的雪静静地下着,炊烟从阿尔莫克莎石碉房缓悠悠地升起”。炊烟的升起是人间烟火的象征,当然也升起了阿尔莫村未来的希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