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郑泰安 张楠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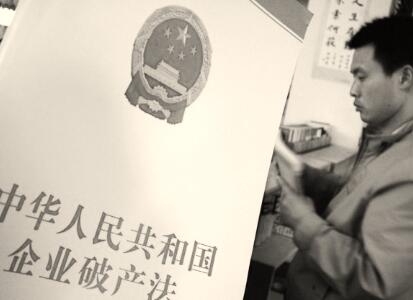
美国法学家庞德认为立法活动是立法者通过理性组织经验的过程。在立法活动中理性和经验缺一不可,二者的相互作用在立法中的具体表现为立法者理性认识客观事物并通过经验加工形成立法理念从而创制法律。立法理念是法律创制的起点,实现理性和经验的辩证统一才可能制定出正当的法、长久的法。企业破产法的问世不仅是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还是市场优胜劣汰经济规律的反映。全面理解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理念,有利于正确贯彻适用与落实企业破产法。
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重理念
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市场主体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引发了一系列债务纠纷。在企业资不抵债时,仅靠民法和民事诉讼法难以应对,因此各国纷纷因地制宜制定破产法。自法的起源来看,企业破产法的立法目的自始即为解决市场主体的债务纠纷,其立法理念的核心在于保障债权人利益。二十世纪以后,随着社会本位理念逐渐流行,各国立法者才开始注重法的社会效应,立法理念也从单纯保障债权人利益向兼顾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方向发展。
1986年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主要针对政府主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在立法上更侧重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并没有对破产企业的债权人予以平等保护,具体表现在劳动债权和国家债权居于破产债权之前。随着经济较快的发展,企业破产法立法理念从着重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转变为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重,优先清偿担保债权,职工工资和其他福利只能从未担保财产中清偿。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并重的立法理念,一方面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使我国企业破产法更好地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保留了原有的中国特色,使企业破产法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亦能维护社会稳定。
破产制度和重生制度并存理念
破产不仅包括破产制度,还包括重整与和解在内的重生制度。现实中,并非所有破产企业都没有存在价值。如果对所有资不抵债的企业都进行破产清算,无疑会增加经济成本和浪费社会资源,这与企业破产法重整与和解制度设立的立法初衷相悖。对此,企业破产清算前给予企业重生的机会尤为重要。重整制度通过企业的转让、合并、分立、追加投资等方式特殊处置债权,在债务公平清偿的前提下实现困境企业的再建和复兴。救济性的重整制度已成为各发达国家市场退出机制的必备环节。
除了重整制度,在制度设计时立法者还加入了和解制度。为了避免破产清算,在法院认可的情况下,通过债权人会议达成妥协,以使债权人在清偿债务方面作出适当让步、以图复苏。和解制度的设立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彰显,也是现实社会发展需求的体现。一方面,“以和为贵”是解决我国国民纠纷的基本观念。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针对债权人数较少、数额较小的中小企业适用破产和解程序就具有现实必要性。破产制度和重生制度并存的立法理念既植根于理论又立足于国情,在保障债权平等清偿的前提下适当救济债务人,给予企业重生的机会,使企业破产法能更好地发挥破产预防和救济作用。
立法原则性与灵活性并行理念
在企业破产法制定以前,我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破产程序上一直受到差别待遇。国有企业破产享受“特殊照顾”,在制度上,破产财产的认定和债务清偿顺序有着特殊规定,在经济上,国有企业破产也有财政支持。而非国有企业破产的规定仅在修订之前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所提及,且条文过于简单,缺乏详细严谨的破产程序设计。这种差别化制度设计使得法官找法、当事人守法存在着困境。既不符合立法原则,也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随着非国有企业破产案件的增多,形成一部适用主体统一的企业破产法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两类企业破产制度真正统一尚需要一段适应期。
因此在制定企业破产法时,立法者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划分了政策性破产和商业破产的界限。对于列入规划等待破产的国有企业,破产法明文规定,“在本法施行前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同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政策性关闭破产工作意见的通知》,规定政策性关闭破产的期限为2005年至2008年。这就意味着,等这些国有企业实施政策性破产后,所有企业都将受到企业破产法的调整,对国有企业的‘特殊照顾’将不复存在。立法原则性与灵活性并行的立法理念巧妙地解决了国企与民企破产程序的差别化问题。
“事移则法异”,法律总能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关系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作为创制法律的起点——立法理念更是如此。从并重理念、并存理念、并行理念出发的企业破产法既与世界接轨又具中国特色;既能保障债权又能救活企业;既满足了改革需求又解决了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