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仁宇

荫宋、辽签下“澶渊之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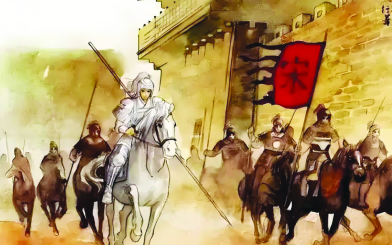
荫行进中的宋军。

荫辽军使者在享受陈酿汾清。
第十五回
汾清酿止双鹤衔杯
汾河清冽酿沧桑,腊月寒威迫酒坊。
寒骨药方融旧怨,双鹤衔杯化雪霜。
汾阳城外的杏花村,一入腊月便被刺骨的寒意笼罩。贾家酒坊在暮色中宛如孤舟,檐角铜铃被北风扯得叮当乱响,连呼出的白气都要在半空凝成霜。百年老杏树枝桠如扁铜叉,挑着褪色的“汾清”酒旗在风中摇晃,字迹早已模糊,却仍倔强地诉说着酒坊的沧桑过往。
贾轩蹲在酒窖第三层,幽暗的空间里,陈年酒香与潮湿霉味交织。他的指尖轻轻抚过刻着“贞观三年封”的酒坛,泥封上蛛网般的裂痕刺痛双眼——这坛酒藏着贾家先祖随唐使西行带回的胡商秘方,渗出的酒气混着硝烟味,与三年前幽州城破时父亲铠甲下的血腥气重叠。
百年来,窖中封存的不只是美酒,更是丝路驼铃与烽火狼烟交织的岁月魂魄。儿时,祖父总会在酿酒间隙,讲述酒坊的故事。那些温暖的回忆里,酒窖充满生机。如今,却只剩下他独自守着这份传承,在幽暗的酒窖中,与历史的余温相伴。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酒窖外传来,打破了令人窒息的静谧。木梯的吱呀声响起,老管家王三的布鞋踏上青石板,腰间铜钥匙串撞出细碎慌音。
“辽军马队进巷了,带头的副将靴底沾着朔州红土!甲缝里嵌着宋瓷碴!”他声音颤抖。
贾轩袖中的宋瓷残片割破掌心——正是去年辽使当着他面摔碎的御赐“雨过天青”盏。瓷片刺入血肉的疼,让他想起父亲咽气前的话:“酒是血酿的,可血不该是酒换的。”
贾轩站起身,动作带起的风拂过身旁陶瓮。瓮身“开宝二年制”的刻字被手泽磨得发亮。那是父亲在高粱减产时,用三成稗子酿成的次等酒。谁能想到,这看似平常的酒,却在幽州之战中救下二十位染寒的辽军伤兵,种下跨越国界的善缘。
寒风裹挟着战马的嘶鸣灌进酒坊,贾轩紧了紧衣领,大步迈向酒坊前院。
前院拴马桩旁,三十骑辽军甲胄泛着冷光。副将耶律斜轸刀尖挑起酒曲布,狼首刀环在晨光中划出弧光。
“贾老板的‘隔年陈’能化雪水为玉露?本将要三十坛为南征饯行。”他的刀柄缠着半幅宋锦“并蒂莲”,与父亲棺中那方残帕如出一辙。
贾轩低头行商礼,袖中辽使摔碎的宋瓷残片硌得掌心发疼。这疼痛,提醒着两国的矛盾。他指向老杏树,枝头冰晶碎落如泪:“腊月本是封坛季,将军瞧这杏树——去岁霜早,头茬高粱收了七成,十年陈仅余六十三坛。”
耶律斜轸的刀尖突然抵住他咽喉:“六十三减三十,余三十三,贾老板是要拿自家酒窖当算盘?”气氛瞬间剑拔弩张。
就在剑拔弩张的僵持时刻,一阵凌乱的马蹄声由远及近。 巷口传来马嘶,几个辽兵抬着担架闯入,疮疖溃烂的小腿滴下脓血,在青石板上灼出焦痕。伤员小腿爬满暗红疮疖,正是朔州湿瘴征兆。
贾轩推开刀刃,掏出晒干的苁蓉叶:“将军若信得过,三日后奉上三十坛‘隔年陈’,另加三坛‘寒骨酿’。”他掏出的苁蓉叶,叶脉血丝蜿蜒如界河地图。“此酒专克朔州湿瘴——将军令堂在云州时,可常去西市买胡商的面脂?”
这话如石子,在耶律斜轸心中激起涟漪。耶律斜轸瞳孔骤缩,刀尖在青石板刻下深痕,恰与地缝中半块界碑残石的“宋”字相交。
夜色渐深,寒风呼啸着掠过杏花村。
深夜酒曲房飘着苦艾香,李伯缺指的右手攥着石磨柄,血藤粉簌簌落入陶瓮。贾轩突然按住老人手腕,从暗格取出锦囊倾倒——七颗带血契丹狼牙坠入石臼,与血藤混作猩红齑粉。
“用辽人狼牙杵磨药,宋土陶瓮盛酒,胡汉血泪化曲。”贾轩举起父亲留下的青铜酒勺,勺柄刻着龟兹乐舞图,“这才是治乱世的药引。”
李伯颤抖着捧出三年前埋于杏树下的“寒骨酿”,坛身火漆印的杏枝纹裂开细缝,渗出铁锈味的酒气。油灯在寒风中摇曳,将两人的影子投射在酒坊的墙壁上。
深夜,酒曲房飘着苦艾香。昏黄油灯下,李伯在石磨前筛血藤粉。他缺了无名指的右手,在月光下泛着青白,那是多年酿酒留下的伤痕。
贾轩盯着混着朱砂的酒曲,十岁那年的记忆浮现——契丹老妪用绣狼头的帕子,包着半块胡饼塞给他,帕角小小的“贾”字,此刻与耶律斜轸刀柄锦缎重叠。
“把三年前埋的‘寒骨酿’起出来。”贾轩挑开陶坛泥封,深青酒液在烛火下泛着铁光,“掺三勺血藤粉,七片苁蓉叶——用耶律洪帐中汉医的方子。”
李伯的石磨卡住,他急道:“少爷是要拿救命药换贼寇的刀?你爹当年就是在朔州城头……”
“父亲送酒辽营时,耶律洪妻子托他带信给李延宗,”贾轩打断,指尖划过石磨波斯纹,“那封信,就在耶律斜轸刀柄里。他们粮草过狼牙谷,唯有我们的酒能解湿瘴。”
李伯沉默许久,最终选择相信。时光在酒曲的研磨声中悄然流逝,转眼到了约定的日子。
三日后,辽营大帐。耶律洪盯着坛身杏枝纹火漆印,抽出腰间银壶,壶底“李延宗印”被酒液泡得发亮。他倒出半碗“寒骨酿”,药香混着酒香散开。
帐外伤兵惊呼:“是朔州老妈妈的草药味!”
耶律洪手指摩挲坛口,良久开口:“你父亲当年在朔州城头,替我妻子挡过三箭。”
贾轩望着酒液里晃动的灯影:“所以将军靴底红土,混着我父亲埋在朔州的酒坛碎瓷。”这一刻,仇恨在酒香中悄然消散。
转眼间,战事的风云仍在继续,新的故事又在酝酿。
景德元年春,枢密院沉水香飘进蒸馏室。身着儒衫的黑衣人摘去斗笠,额角“神卫军”的刺青若隐若现:“澶州前线急报,杨六郎缺马料,寇准要你在酒里掺乌头碱。”
贾轩添了勺新漉的酒,酒花绽开如并蒂莲。“上个月耶律洪送回的空坛,坛底都刻着契丹文的‘和’,像两只交颈的鹤。”他舀起一碗酒泼在地上,听着“滋滋”声说:“宋军‘壮行酒’掺幽州枣树根,解水土不服;辽军‘祛湿酿’加云州黄芪——上月他们痢疾,可是我们商队送了三百坛黄连清酒。”
黑衣人若有所思,默默退下。
岁月流转,转眼到了景德二年的腊月。
景德二年腊月,澶州城头。积雪混着杏花碎瓣飘落。贾轩捧着玉壶春瓶穿过宋军甲阵,瓶身双鹤衔杯图泛着微光。那是用辽瓷白釉与宋瓷青料合绘,匣钵底还埋着契丹狼首刀残刃,寓意着化干戈为玉帛。
萧太后接过酒杯时,金错刀划过“澶渊之盟”的绢帛。“听闻贾先生的酒,能让耶律洪的副将放下屠刀?”她问。
贾轩望向榷场灯火:“去年秋末,耶律斜轸的战马在杏花村染了风寒,是李伯用酒曲敷了三日才痊愈。如今他的刀柄上,还缠着我送的酒坊粗布。”
酒液入喉,萧太后轻笑:“当年太祖皇帝杯酒释兵权,如今你用酒释干戈。”她望向城外渐浓的暮色,契丹商队的驼铃声里混着宋商的算盘响,“榷场的‘双鹤酒肆’,可是宋酒用辽瓷盛,辽酒用宋盏装?”
贾轩点头,目光落在城楼下的老杏树——枝头已泛起粉白,像极了父亲临终前说的“和平的预兆”。春风掠过酒旗时,他忽然开口:“酒本无国界,就像这杏花雪,落在宋境是宋词,落在辽境是胡笳,化了都是滋养土地的水。”
百年后,《汾州府志》载:“景德年间,贾氏酒坊以‘汾清’为媒,通宋辽之好,设榷场七十二,活边民十万余。其酒曲秘方藏于杏花村老杏树下,遇旱不涸,逢涝不腐,传为‘和平之酿’。”
每当清明时节,汾阳百姓抬着酒坛祭拜老杏树。褪色酒旗在春风里愈发鲜艳。有人说,那酒香里藏着战马卸甲的声响,藏着胡商与汉贾的笑谈,藏着千年前那场杏花雪的温度——当酒液入喉,所有的刀光剑影,都化作了舌尖的回甘。
而酒窖第三层的老坛旁,不知何时多了块无名碑。苔痕斑驳间,隐约可见“以酒为媒,止戈为武”八个小字,被岁月磨得发亮。它静静地立在那里,见证着这段传奇的历史,也诉说着和平的珍贵与美好。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