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李永才《南方的太阳鸟》
■ (重庆)吕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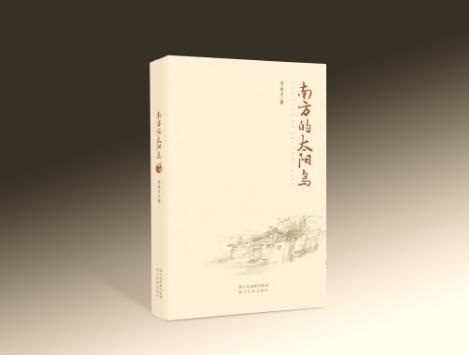
从《故乡的方向》算起,《南方的太阳鸟》已经是李永才的第六部诗集了。如果我没有记错,此前他还曾给读者捧出过《城市器物》、《空白的色彩》、《教堂的手》和《灵魂的牧场》。
“南方”是诗人的地理坐标,并不是诗笔的地理坐标。“四鸟绕日”的太阳神鸟是古蜀人的图腾,倾心自由、向往光明的太阳神鸟,是诗人的精神坐标。永才说:“我希望自己是一只充满神性的鸟。”
我想起戴望舒,想起他那首被称为“最纯的诗”的《乐园鸟》——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
昼,夜,没有休止,
华羽的乐园鸟,
这是幸福的云游呢,
还是永恒的苦役?
这就是诗人的宿命:飞着,寻找着,无休止地追寻乐园之境,上下求索而无所依归,“寂寞”,而又“永恒”。
诗人是常人,他在写诗的时候又不是常人。当他提起诗笔,他就洗净了尘世的烟火与喧哗,摆脱了常人的俗气与牵挂,“肉眼闭而心眼开”,在他的内在世界飞翔。诗人的世界是诗的太阳重新照亮的世界。太阳神鸟正是诗人的象征。
永才出诗集是2011年以后的事,其实,他很早就开始写诗,他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校园诗人。八十年代是中国的温暖年代,也是新诗的彩色年代。在四川师范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永才,钟情于缪斯:写诗,办诗刊,组织社团。在他所交往的诗友中,有好些当时也和我打过交道。前天,当年的校园诗人田家鹏打听到了我的微信号,和我重新联系上了,我和他都很高兴。当年他写过一首叙事诗《继母》,我读后受到震撼,这首诗大有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韵味,我建议他寄给《诗刊》。主持《诗刊》工作的邵燕祥收到后也非常欣赏,在1983年第2期的《诗刊》推出。1985年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一得诗话》,也细读了《继母》。去年,《诗刊》纪念创刊60年,以编年史的形式出版《〈诗刊〉创刊60年诗选》,在1983年就选了这首诗。
家鹏在巴,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而永才在蜀。但是,永才是去到蜀国就读和工作的巴人,他的家乡在涪陵。所以,在他的诗里,在他的身上,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巴人气质:热情、豪爽和耿直。八十年代的校园诗人是一个很有风采的群体。从这里走来的李永才,在写诗上的艺术积累是丰厚的,读他的诗,会体味到他的手腕的纯熟和对现实的淘洗工夫。读读《和平菜市》吧,最寻常的生活,最平凡的角落,诗人居然就可以寻觅出诗意,提炼出诗思——
守车老人坐在门口,数十年如一日
坐实的椅子,坐着坐着就旧了
对面的洋槐花,如老人头上的白发
风吹过一次,槐花就落一次
岁月的流逝,生命的流逝,以及岁月与生命的流逝带来的沧桑,尽在诗外。日子在旧,白发在落。这就是诗,这就是诗家语。如果用日常语去解读,就会很愚蠢,很无奈,也很无效。诗是难以说破的,只能以心会心。
永才的诗,无论写明媚还是忧伤,无论是锦城走马还是梦枕江南,无论是短曲还是长制,都显示了诗人的才华。并且披露出,这不是随意涂鸦的写诗的人,而是一位有理论修养,有自己美学追求的诗人。
永才对我说:“我是重庆人,却在成都做事,你是成都人,却在重庆讨生活。”此言不虚。八十年代,在北京开全国教代会,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韩邦彦曾经在前往人民大会堂的大巴上给全团的人说 :没有川西实验小学,没有成都七中,就没有今天的吕进教授。在重庆直辖之前,我还没有多少在异乡的感觉,直辖以后,重庆和四川“相去日已远”,我也有了些许的漂泊感。
《四川百科全书》是29卷的大型工具书,1994年开编,一直到重庆直辖后才得以完成。1998年5月21日,在成都隆重首发。因为我是总主编,所以我所在的西南师范大学的校长也应邀出席。我做编辑工作总结报告以后,《四川百科全书》编委会主任、省委副书记秦玉琴讲话。她说:“这个工程完成得很好,以后还有这样的大型文化项目的话,我们还要请吕进教授主持。”我在心里有些发酸:谢谢美意啊,但是遗憾得很,不可能了,这是我为故乡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了。
所以,《南方的太阳鸟》那些书写芙蓉城的篇章,特别搅动我这个游子的乡思。这是《大慈寺》中一个诗节——
秋后的老房子,红墙黄瓦
那些历史的物证
与眼前的素材,格格不入
后现代的窗门,挤得它
只剩下一只佛脚,一点慈悲
在其间流连
四川省作家协会的宿舍就在大慈寺路,那里和《四川文学》、《星星》编辑部所在的布后街,是我儿时的圣地。现在,后现代破门了,把那些“格格不入”的挤压成历史。时代在变,故乡在变,诗人真敏锐啊!
永才在《后记》里说到“写诗的难度”,这也是我注意的话题。近年国内的高三学生语文复习题,往往喜欢选用我的诗论作为题目之一。最近看到2015年的复习题,二十道题里又有一道是我几年前发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新诗的“变”与“常”》。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要“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提出这个问题的语境是互联网+诗歌的时代:网络赋予写诗的无限自由和无限方便,每天都有巨量的诗跳到人们的面前:真伪共存,优劣杂陈。
有人欢呼,看吧,新诗已经复兴了。在我看来,当下的新诗离“复兴”还八竿子都打不着呢。诗人、政界、商界共同制造的热闹很可疑,热闹的背后是寂寞。令人目不暇接的采风、诗会、诗歌评奖、诗刊给人一个“繁荣”的假象,其实是繁而不荣。
翻翻中国新诗发展史,可以说,在已经过去的100年当中,除了新时期的诗是长出来的以外,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诗是嚷出来的,目下许多诗则是仿出来的,许多新诗理论是想出来的。比起相互模仿,比起倾吐个人身世,倾倒原生态情感,用具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诗家语去言人所欲言而又未言,的确是具有相当难度的。
所以,当我在《南方的太阳鸟》的《后记》里读到永才这样的宣示的时候,我是很赞同的:“随时提醒自己要有更多的现实关怀和人类永恒的主题。更多地选择一些关乎人类社会,自然与生命的公共题材,加以提升和转化。而不再去写那些小情小景,和个人化小情感的东西。这或许就是我持有的诗歌审美向度。”我觉得,永才正是在探寻通往大诗的路,对于写了30年诗的他,这应该是一种必然。
真正的诗人,会用他的芬芳滋润同时代人的心灵——
诗人呐,请让我点燃一根火柴
照亮你夜行的孤舟
宛如怀抱清风的明月,穿过桥头
就可以抵达,对岸的灯火
只要栀子花还开,像浪花一样
在时光的体内,总会保持诗人的芬芳
——《诗人的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