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辛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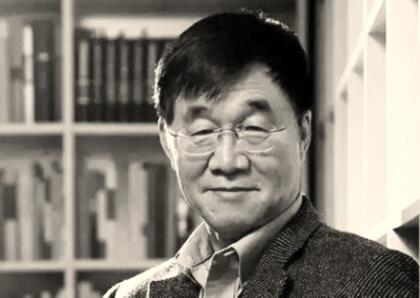
《康德传》开篇第一句话是:“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学说的历史外,自己就再没有别的传记。”这句话自1981年读过后,一生从来没有忘记过,常在心中自我咏诵,也常常在耳边响起,似乎成了自己一生无形的座右铭。
问:韦森老师,您好,学界一般对您的了解似乎始于2001年您从海外学成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从那时起,您一直活跃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园地,从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直到现实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研究,乃至西方历史文化哲学基本学术原典的译介,您均有诸多成就与卓见。读者或许对您的早年学术经历更感兴趣,能否请您说一下早年的经历?
韦森教授:好的。我于20世纪年50年代出生在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个乡里以及后来的公社里的小干部,母亲是个不识字但非常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1962年年我开始上小学。因为长我两岁的大姐已经教我识字了,一到一年级的课堂,我对一年级薄薄的语文课本一下子就能从头背到尾,于是老师叫我直接跳级到二年级。因为一年级基础没打好,直到现在我拼音字母四声还分不大清楚。三年级开始,我就开始读《小五义》、《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这也培养了我少年时期读小说的喜好。记得小学毕业时,自己大约读了五六十本比较大部头的各类小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以及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
小学毕业后,“文革”开始了,我也就无机会正常继续上中学了。邻村的一位大哥哥趁“文革”混乱从我们县中图书馆弄来好几架书。这倒成了我在“文革”时的“图书馆”了。这期间,我通读了《鲁迅全集》20卷,还研读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等。当时也看到了书架上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但读不大懂。读了这些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文学家的作品,奠定了我的文字功底,也使我极其苦闷乃至绝望。1968年左右,我小小年纪参加我们县一个保守派(保王效禹派)造反队,成了其中的“首席笔杆子”。
记得大约是1972年左右,中学又开始复课了,我因是县里“保王派”造反队的笔杆子,被“照顾”分配到单县二中上高中。上了两年高中,毕业后在城里“安排”不了工作,我又回到自家村里去劳动。
回村后,我当了一年左右的生产队队长和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当生产队长时,看到村里的每个社员都出工不出力,时时偷懒,自己干着急,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好好干活,等年底收成好了,每个工分才更值钱,大家才能分到更多的东西。经常开会,说破了嘴,但好像从来没人听。这使我非常苦恼,也百思不解:一个生产队里大家都偷懒,出工不出力,地里的庄稼长不好,到年底都挣满工分,每个人又能分多少东西?到二十多年后,我在悉尼大学做经济学博士论文时,才明白了这原来是个劳动共同体的激励问题,是一个所有社员在劳动投入、偷懒和收入分配上的囚徒困境博弈,才开始意识到这原来是经济学家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央计划体制非可行的根本性问题。我博士论文第一章所做的理论模型的现实原型,恰恰就是在我记忆中的这一生产队中社员劳动投入、偷懒和队长如何通过开会和政治学习来激励社员干活的问题。这一博弈模型的中文译文,发表在了《经济科学》1995年第5期,题目叫“产权非个人化条件下生产者联合体成员的劳动投入行为”。
尽管做生产队长时我们村的工分分值差不多是邻村最高的,每工分(一个工作日分值)两毛八分钱,但觉得整天给村里的老少社员们做劳动投入的那种“激励博弈”,实在没意思,后又经父亲的一个老战友的介绍,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没进车间当工人,直接进了厂生产办公室,做统计和工厂秘书行政工作。我还记得,因为我们厂是省供销社口的“双学先进单位”,我曾伴厂长到省里和邻近县里开会、介绍先进经验。在单县棉花加工厂做统计期间,“批林批孔”运动来了,中央号召全党学六本马列的经典书。免费得到了六本白皮的马列著作,就开始啃读起《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起来。从那时开始,我也从少儿时喜爱读文学作品转而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了,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哲学家康斯坦丁诺夫的一本《历史唯物主义》。那本书我读了多遍,还在朋友借来的书上画满了批注。随后也开始啃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但实在读不懂,硬着头皮读了几章就放下了,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在这一时期,自己一边读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的书,一边看到“文革”后期国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也就在那时候,我与我们县里的一些小学教师和几个读书人自发形成了一个类似今天的“沙龙”似的聚会。这段时期的经历,陶冶了我们那代人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尽管当时自己还只是个临时合同工,尽管是一个小工厂一名文员,但自那时起就很少关心自己未来做什么,挣多少钱,而是整天与一帮哥们谈论国家高层政治风向变动,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走向。
大约是1977年秋天,政府下文件说要恢复高考了。虽然自己只是正儿八经上过5年小学,后来断断续续地读了点“革命”中学,知识残缺不全,加上开始还不知道结了婚政府还是否允许报考,但我还是买了复习材料,抱着不妨试一试的心态,偷偷复习了三个月,并且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第一次考试我就上初选榜了,但是因为分数不是太高,加上自己所填写的报考志愿是国内三所顶尖大学,包括复旦,结果1977级入学没被录取。几个月后,又参加1978级的入学考试,以县里文科生考试很高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问:你们这一代学人大致多有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曾经如此地接地气,对养育你们的土地乃至国家、民族怀有深情,由此萌生各自的学术抱负,才有后来基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学术思想景观。那您又是如何选择兼具人文哲学底蕴的经济学研究作为日后的学术旨趣的?
韦森教授:进了山东大学,进到了图书馆,仿佛看到了书的海洋,当时真有一口吞他半边海湾水的雄心。整天泡在图书馆中,也开始做点研究,尝试着写起文章来。尽管大多数课都没好好听,但各门成绩大都还是A。在大学期间真正下功夫的,只有两门课:一是上了一年半的《资本论》研读课:二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来山东大学开了一学期的黑格尔的《小逻辑》讲解课。听了张世英教授的黑格尔哲学的讲解课,也随之研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一时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粉丝。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方法很大程度上源自黑格尔,且他的《资本论》写作的方法基础是黑格尔的逻辑哲学,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研读课的期末考试中,曾尝试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来写答卷,受到了讲课老师的赞赏,竟然意外地给了个满分。
在大学读本科期间,读得较多的书是哲学书,非常沉迷黑格尔哲学。但大约在1981年年底,偶然从图书馆中借到了苏联哲学史家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一口气读了下来,铭感至深。读到深处动情处,竟一个人在寝室中呜咽起来。接着我又细细研读了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这成了我在大学读本科期间觉得阅读收获最大的书。读了古留加的《康德传》,又接着借阅了同作者的《黑格尔小传》,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读了《康德传》,尤其是读了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之后,康德随即成了自己一生永远不倒的偶像。《康德传》开篇第一句话是:“哲学家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学说的历史外,自己就再没有别的传记。”这句话自1981年读过后,一生从来没有忘记过,常在心中自我咏诵,也常常在耳边响起,似乎成了自己一生无形的座右铭。反而,读了《黑格尔小传》之后,就像个长大的孩子不再相信儿时的童话故事一样,自大学毕业到2011年,很少读黑格尔的东西。只是到前几年研读德国法制史和和德国经济史时,又读了一遍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读过古留加的《康德传》和李泽厚的《批判铒学的批判》后,我马上从商务印书馆购买到了《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只有蓝公武的译本。康德晦涩难懂的哲学思想,加上蓝公武的半文言文译本,使自己读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多年来在国内又没有找到其他译本,对康德哲学一直是从“望而生敬”到“望而生畏”,只能从李泽厚等哲学家的二手的介绍来理解康德的思想。直到2001年从剑桥大学访学归来后,我才买到了韦卓民先生的译本,结合后来从台湾购到的牟宗三先生的译本,以及N.K.Smith的英译本,才勉强啃读下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Lewis W.Beck 英译本)和苗力田先生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虽然康德哲学断断续续读了二十年,但自忖对自己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还是康德以及后来的维特根斯坦。譬如,自己2002年出版的《经济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的小册子,尽管在书中使用了元伦理学尤其是黑尔(Richard M.Hare)推理方式,并用现代经济学乃至博弈论的方法做了一些经济伦理学的探讨,但整本小册子所展示的还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义务论的道德观。
在大学读本科期间,一边读书,一边学着做研究。到大二时,我开始写文章,不断向外投稿。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大致做了三项研究。最早做的“研究”,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问题”。记得这项研究我投入了大量精力,几乎搜读了当时能发现的所有中文文献,引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大致自己能找到的观点,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那时写文章既不能像现在这样保存电脑文档,也不能复印保存。只能在方格子稿纸上一遍遍地抄写,爬完格子后将稿件通过邮局外投。这篇关于贫困化的稿子,我投了几家国内大刊物,都没中。最后,当时乃至现在仍蛮权威的经济学刊物《世界经济》从我至少上万字的长文中摘录了不到一页,以我“李全金”的原名发表在《世界经济》1980年第11期上的来稿摘编中。这应该是我一生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字稿了。第二项研究是关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并在1980年大二期间就写出篇短文章《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生产的目的性》,也以我小时的原名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6期上。这应该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全文文章。第三项研究是我在大学期间所写的本科论文。文章写得很长,原文题目是《论经济科学的方法论》,是一篇打字稿,曾全文刊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2年内部期刊的某一期上。这篇文章后来曾分上、下两期分别发表于1982年第6期和1984年第3期《文史哲》上,上篇的题目是《对经济科学的些基本范畴的初步理解》;下篇的题目则是《试谈经济科学范畴的逻辑体系问题》。从这两篇文章中,今天仍可以解读得出来,到这时候,我对经济学这门学科认识,还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且当时天真地把自己一生的学术目标确定为撰写一部像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样具有新范畴逻辑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这篇毕业论文中,也大致能解读出我当时经济学思考的康德哲学转向:从哲学本体论上把握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马克思曾在他的著作中所使用过的“社会生产机”或“经济机体”概念,从而不是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二因素或加上劳动对象三因素的结合,而是把生产力理解为生产能力(有点相当于现在当代经济学屮所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把生产方式理解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的结合方式和运用什么样的劳动资料进行生产的方式,并把生产关系理解为在人们社会生活资料的生产中以物为枢纽的所有相互结合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尽管今天我们己经不再使用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来进行社会科学和经济学述说了,但现在想来,这实际上有置否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样的斯大林主义的机械唯物史观的意思。
问:没想到您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初学者如此偏重哲学著作的研读,这也为我们解答了您今天的学术研究不同于一般经济学者的区别其来有自了,您之后的职业生涯的起始正是整个中国学术界启蒙与重建的年代,我们今天的读者并不了解您在此时期的学术状况,可否详述?
韦森教授:1982年本科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在《东岳论丛》编辑部做了几年的经济学编辑。开始在山东社科院工作期间,资料室所有的参考资料也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再加上《马克思传》和苏联阿多拉茨基主编的《马克思年表》。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50卷本只出版了46卷),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并把马克思论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经济、按劳分配、异化、无产阶级贫困化、利润率下降趋势等等条目分门别类做了几箱摘录卡片,随即也在这极其安静无扰的环境中写出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经济科学》,1984,此文曾获山东社联优秀学术论文一等奖)、《生产力概念再探讨》(《学习与探索》,1985)、《马克思著作中生产力概念的两种含义》(《求是学刊〉,1985)、《马克思著作中的社会生产机体”概念》(《河南大学学报》,1984)等文章。今天回头再读这些自己的早期文章,虽然觉得这些概念和话题都是“过去式”了,但似乎仍有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意义。
在大学毕业时,我是真心真意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在1982到1985年间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由于有本《马克思传》和《马克思年表》在手头,在一个极其安静无扰的环境中,完全进入了马克思的思想世界,像跟随着马克思一样观看了一遭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把马克思的所有观点放在他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来理解,就显得格外清晰。我生来记忆力就不是太好,但到今天却能仍然记得一些马克思哪年到哪里,出版了哪些书,写了哪些重要文章,文章的观点与之前之后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读完马克思,我深深感到马克思是个关心人类命运和福祉的伟大的思想家,但他毕竟不是神,也有一个思想演变乃至某些思想和观点的自我否定和扬弃过程。这些年研究马克思的成果,差不多到十年后我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写作自己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导言时,才较系统地讲述了出来。这段时间在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时我的最大理论发现是,马克思于1843年移居到巴黎后结识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魏特林、蒲鲁东以及恩格斯,形成了他早期的对共产主义和未来社会的信念。正是这些信念使他与恩格斯起在1848年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对人类的未来社会提出了一幅比较详细的理论图景。他们写作《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还不到30岁,而恩格斯在1947年10月到11月间写作《共产主义原理》25个问题时,也才不到28岁。而这两位28岁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所讲的这些原理和思想,却构成了后来各国共产党的主要信仰基础。然而,许多研究马克思思想史的学者和政党宣传家没有注意到,或者即使认识到也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自马克思1849年移居伦敦开始研究经济学后,他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发表的意见越来越少,尤其是到他开始写作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阶段,他基本上很少谈论未来社会的理想了。
譬如,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只是在第一章最后一节中论商品拜物教中谈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概念时,有点对未来社会的抽象预测和描述。另外,当时我发现,按照《资本论》三卷的成书时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卷成书的次序是:第三卷成书最早,第二卷其次(二、三卷均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编辑出版的),而第一卷最晚。令人深思的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还在许多地方谈了他自己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和憧憬;第二卷就少了很多,但也有几处。但到了第一卷,其中只有第一章最后一节中谈自由人联合体了,且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模糊。到1867年之后,马克思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好转第一卷出版后收到了一笔稿费,又在他母亲逝世后继承了一笔遗产。这样马克思本应该坐下来修改、完稿和出版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下转03版)
学者名片
韦森,原名李维森,山东省单县人。198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9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从悉尼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1年回国正式执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2000年至2001年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2006年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高级客座研究员。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外有影响的媒体上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
主要学术专著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格致出版社2009年),《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中信出版社2012年)。与汪丁丁和姚洋合著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自1987年以来,分别获教育部、国家体改委、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论文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三项,优秀论文奖一项。